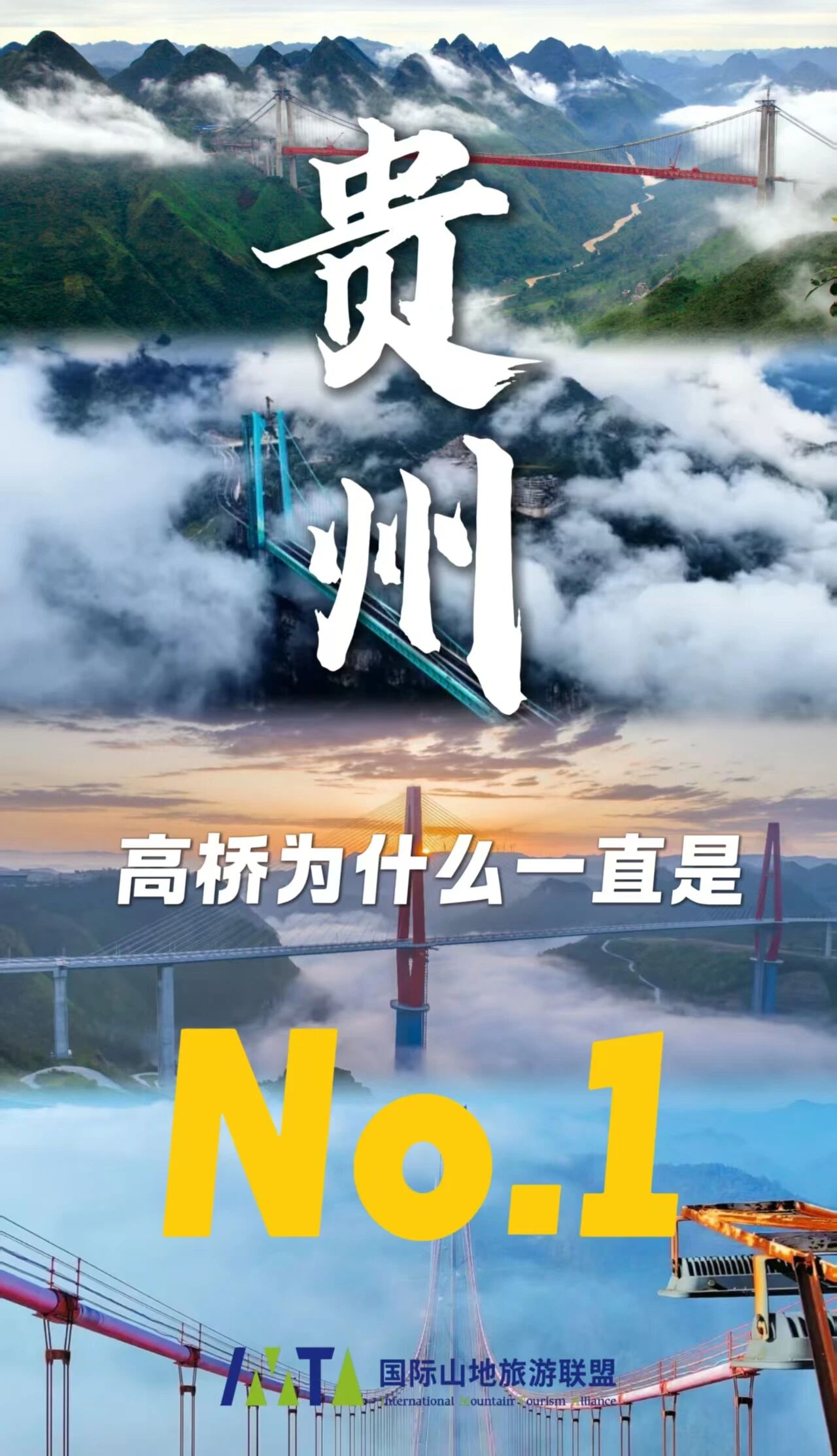
世界第一座高桥正式通车了!当人们听到这一个消息,或许眼睛都会聚焦到地图上的某一个地方,没错,就是贵州。
这座横亘在花江大峡谷之上的钢铁巨构,用一组震撼数据重新定义 “世界之最”:全长 2890 米,1420 米主跨径登顶全球山区峡谷钢桁梁悬索桥榜首;桥面距水面 625 米,相当于 200 层高楼直插云端,“高度 + 跨径” 双料冠军的头衔,让它当之无愧成为 “横竖都是世界第一” 的超级工程。
而这,已是贵州第二次刷新世界桥梁高度纪录。为何偏偏是贵州?一切的答案藏在这片土地 “天崩开局” 的命运里,更藏在它逆势翻盘的智慧中。

花江峡谷大桥
图源: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李佳隆 胡应锋
01 天崩开局
/喀斯特地貌里的 “绝境” 与 “机遇”/
提起贵州,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 是刻在地理基因里的标签——全省 92.5% 的土地被山地与丘陵覆盖,其中61.9% 的区域是喀斯特地貌。
曾几何时,这里是 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” 的贫瘠象征:崎岖的山路绕着山梁转,从山的这头到山的那头,若没有桥梁,只能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数小时,谷底是江河的绝美风景,更是阻碍两岸交流的天堑。
可很少有人知道,而贵州正是这些高耸入云的山体,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高桥的基础。

20亿年前,贵州区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,也就是古地中海。而后在地质板块的不断运动,在贵州高原地界,先后发生了21次性质不同、规模不等的造山运动,而其中的升降运动,便将传说中的古地中海,不断抬高地层,大约在中三叠世晚期(差不多距今约2-3亿年)冲出海平面,海水开始退出贵州。
在晚三叠世(差不多距今2亿年)的一次升降运动,让自此贵州高原完全隆起形成了陆地,最后古地中海的贵州区域,变成了平均海拔1000多米高的贵州高原。
这么简单就形成了贵州高原了?
当然不是,贵州山体崎岖不平,沟壑峡谷众多,还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,他的形成原因可不止因为升降运动哦~还有褶皱运动。褶皱运动,也就是将陆地、山地不断挤压,导致地层变形,变得曲折。
几亿年前的武陵运动、雪峰运动、广西运动,让贵州的地层变得崎岖。最后在6500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,以断块活动重塑地貌:地垒地堑构造切割古地层,多级夷平面与多级河谷阶地形成间歇性隆升。
花江大峡谷的峭壁、黄果树瀑布的跌水,以及织金洞、双河洞、珍珠洞等地下岩溶奇观,都是这场仍在持续的造陆运动的杰作。
其中花江大峡谷位于贵州关岭、贞丰交界处北盘江从峡谷的深处穿流(花江大峡谷是北盘江大峡谷的其中一段),这片峡谷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的地区呈现出峰峦巍峨、怪石峥嵘、错落弯环、峭崖竞秀的峡谷风光。同时它也是贵州高原最大的峡谷。
而山高谷深的花江大峡谷,将安顺关岭与黔西南贞丰分隔在北盘江两岸。如果关岭到贞丰没有通途的高桥,两地到达,需要环绕一圈有一圈的盘山公路,从山上环绕到山下,又从山下绕到山上,两岸风光虽然迤逦,但出行却成了当地致命的难题。
恰恰是这亿年磨就的崎岖蜿蜒的山体,为贵州埋下了建造世界高桥的伏笔。别人眼中的 “阻碍”,在贵州这里,成了挑战工程极限的 “天然考场”。但高桥的建立,也需要强大的基建能力,而这另一要素便是来自基建狂魔:中国的坚持与努力。
02基建破局
/中国智慧如何架起"云端天路"/
举世闻名的成就,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所有的成功,都是 “逆天改命” 的硬实力。若要谈及中国的桥梁,其实看一部数据便可认识中国基建的厉害。
根据2024年《中国公路桥梁发展报告》:截至2024年,中国现代桥梁总数已突破100万座,其中公路桥梁90余万座、铁路桥梁21万余座,总量占全球现代桥梁一半以上。按县域平均计算,每个县拥有近千座桥梁,形成“出门即见桥”的密集网络。
从规模看,特大桥(单跨≥150米或总长≥1000米)数量达1.4万座,年均新增超千座;在全球各类桥梁排名前十的榜单中,中国桥梁占比均超70%,其中,在全球前10名最高桥梁中,中国占据8席;中国桥梁的“长”,是实打实的“世界领先”:全球10座最长跨海大桥,中国占了7座;10座最长高铁桥,中国占了9座。
大家耳熟能详的港珠澳大桥、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、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……都是世界领先。
中国地大物国,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会遇见各种地貌,而长期作业的中国基建,在一座座桥梁的建设中,不惧风险,敢于创新,勇往直前,不断攻克各种“不可能”,在喀斯特地貌、强台风区、高寒冻土等极端环境中屡创奇迹。
而这次的花江峡谷大桥,是又一次挑战,但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对症下药。花江大峡谷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峡谷,峡谷内部的气流,风速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14级,而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建立的第一步,便是如何稳定的立在云端?

云海中的花江峡谷大桥
图源: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李佳隆 胡应锋
大桥建设初期便早早的进行风洞实验,测试并寻找最有的桥梁结构形式以及抗风措施。因此多番尝试的结果便是:多普勒激光雷达测风系统进行24小时职守,随时检察峡谷的天气情况。再对桥身进行“流线型钢桁梁+中央稳定板”的抗风措施。
流线型钢桁梁有效的降低了峡谷之中的风荷载,而大桥中央2米高的稳定板,则消解了90%的横向风振,有效降低了气流对大桥的影响。
大体积混凝土浇筑,温差控制很重要。花江峡谷大桥混凝土总用量近50万立方米。攻关小组自主研发智能温控系统,通过提前埋设冷却水管和智能芯片,在手机或电脑端,对浇筑时的内外温差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。
高桥主缆,被誉为悬索桥的“生命线”。花江峡谷大桥主缆,每根包含217根索股,每根索股由91根直径5.7毫米的高强钢丝组成,投入使用的钢丝总长度达9.3万千米,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多。大量主缆钢索中却藏有智慧,主缆中有3条智慧缆索,引入了北斗高精度定位,并带有光纤传感器,相当于肉体中的中枢神经,对大桥无时无刻的进行监测。
三条缆索各不相同,一条负责温度的监测、一条负责湿度,而最后一条便是监测缆索受力的变化。
正是这样的中枢神经,将这座由93段钢桁梁拼接而成,标准节段重约215吨的世界第一大高桥能够实现毫米级调控以及一键起吊。
正是这些对于喀斯特峡谷地貌量身定制的高桥建设技术,不仅突破了贵州山区的难题,更是成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的提供了中国式方案。
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,中国基建的每一次突破,都是拼劲全力之后的顺势而为,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世界第一。中国基建用实力证明:没有跨不过的天堑,只有不敢想的突破。
03天堑变通途
/开启了秘境的探寻之旅/
山与山之间,因桥梁而相连;数万座山连成一片,便成就了人们所说的“人造平原”。随着道路的拓展,贵州不再被视为贫穷的代名词,而是成为了一个备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。
桥梁连接的不仅是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,更是贵州人民所希望展示的美景,以及世界各地对山地风光充满向往的旅行者。
近年来,桥旅融合成为贵州旅游的一大特色,一座座高桥不仅促进了文化旅游的发展,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。
坝陵河大桥的低空跳伞、平塘特大桥的桥梁博物馆、龙里大桥的高空玻璃栈道,以及花江峡谷大桥的高空蹦极、高空跑道、高空咖啡馆和灯光秀,还有那绝美的水瀑……花江峡谷大桥更是将贵州的自然文化融入其中。

贵州龙里河大桥 图源: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
晚三叠纪时期,花江大峡谷地区因地质运动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海域,后因地质抬升,导致海洋生物大面积缺氧死亡,留下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化石。
桥旅融合将这些自然特色与周围的三叠纪地质公园完美结合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闭环。
桥梁的建设不仅仅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文旅融合,其影响遍及整个贵州省,深入到贵州的每一个角落。
生长在贵州的孩子们,或许从小就见过山中竖立的标语:“石漠化,从一棵树做起”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守护喀斯特生态家园”。对于贵州的农民来说,怪石嶙峋的石头曾是他们的心头大患。
当地人曾说:“石头开花,马长角。
换句话就是“大雨一来,泥土一冲,光秃秃的石头,就像遍地开花冒出来;因为不通路,家家养马驮物资,高高的马鞍,像马长出的一个角……”这是贵州黔西市的某位村支书的描述,但这几句话却道出了贵州喀斯特石漠化的真实状态。
严重的喀斯特石漠化使得农作物难以在贫瘠的土地上存活,以前的贵州常常出现“一抔土,一碗饭”的种植情况。传统的耕作方式如刀耕火种,只会加剧喀斯特石漠化现象。然而,交通的便利为这一切带来了一些改变。
石漠化地区竟成了徒步爱好者追寻的 “秘境地标”?
近年来,贵州徒步热潮席卷全国,无数人跨越千里而来,只为亲身体验喀斯特地貌独有的粗粝与灵动。
当传统观光景区的打卡式游览渐渐失去新鲜感,藏在群山深处的山地徒步路线,正以最原始的姿态,带人们解锁贵州的另一种美——而那些曾被视为 “生态难题” 的石漠化风光,也意外成为这场徒步热里最独特的风景。
安顺龙宫附近的铜鼓荡,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处。从龙宫景区出发,沿着山间小径蜿蜒向上,约莫半小时便能抵达这片 “奇石秘境”。
不同于景区里规整的步道,铜鼓荡的路藏在裸露的石灰岩间,脚下的岩石被岁月磨出深浅不一的纹路,踩上去带着几分硌脚的真实感;抬头望去,成片青灰色的石峰拔地而起,有的像被巨斧劈开的断面,棱角分明;有的则被风雨侵蚀得圆润光滑,仿佛大自然亲手雕琢的艺术品。
阳光穿过稀疏的灌木洒在石面上,光影在凹陷的岩缝间流转,竟让冰冷的岩石有了几分温柔的质感。
站在最高处的岩石上远眺,能看到山中的洞口隐约藏在绿树间,脚下的石群绵延向山谷深处,与远处的峰丛连成一片,既有石漠化地貌的壮阔,又不失喀斯特的灵秀。
除了铜鼓荡,安顺的桃子凹、牛倒岩,六盘水六枝的龙脊山,也都是徒步爱好者的 “宝藏目的地”。这些地方的共同点,便是那成片裸露且高低不一的岩石——它们曾是喀斯特石漠化的印记,如今却成了贵州徒步风景里最独特的 “名片”。
当人们踩着岩石、穿过灌木,在汗水中感受风与石的对话,才真正读懂:所谓美景,从不是只有绿水青山一种模样。那些在自然变迁中形成的 “不完美”,或许正是另一种极致的浪漫。不过,在惊叹于石漠化景观 “火星地表般” 的奇异之美时,我们也不能忘记它曾带来的生态挑战。
好在这些年,贵州从未停下治理石漠化的脚步:通过科学规划与生态修复,如今的石漠化土地早已 “各得其所”—— 有的种上了耐旱的火龙果,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;有的成了花椒种植基地,秋日里满坡的花椒透着浓郁的香气;有的培育起百香果,藤蔓间垂落的果实酸甜多汁;而另一部分景观奇特的区域,则被打造成观光区,让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实现了双赢。
随着石漠化景观 “出圈”,贵州的山地旅游也迎来了全新的热闹。如今在贵州,“山中堵车” 早已不是新鲜事:徒步队伍在半山腰排起长队,大家相互搀扶着穿过石缝;摄影爱好者堵在瀑布中间,等待前一个人完成风景的拍摄;溶洞里的浆板队伍缓慢进洞,头灯的光束在钟乳石上折射出奇幻的光影……这些充满烟火气的 “拥堵”,恰恰是贵州山地旅游蓬勃发展的缩影。
交通的便利为这片土地打开了新的大门,也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贵州:它从来都不是所谓的 “穷山恶水”,只是需要时间与努力,等待蜕变的时刻。当花江峡谷大桥的钢桁梁在阳光下泛着冷光,当徒步者的脚步叩响铜鼓荡的石灰岩,当溶洞里的浆板划破地下暗河的静谧,贵州用一个又一个 “世界第一”,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疑问:它的 “多第一”,从不是偶然的幸运,而是山河馈赠与人类智慧的双向奔赴。
一审:袁佳利
二审:鲍港
三审:张翼晶










